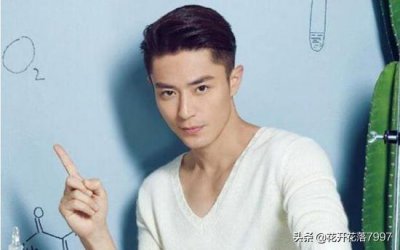追寻那离我们并不太远的潴龙河之二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我的家乡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地居博水之野故名,穿越历史的时空的隧道,去领略千年古县那曾经的江天一色的风采:博野这块神奇地土曾经流淌着如博水、孝义河、唐河、赵家河等诸多美丽河流,然而,时过境迁,沧海桑田,还有离我们消失很近的那条古河流----潴龙河,如果将这些河流像珍珠一样串起来,就能构成一个博野县古代河流的历史博物馆,深切缅怀远古那曾经“水天一色”的地域灵魂和名片
历史老人不禁要问:上苍为啥如此眷顾博野这奇的土地,致使水系如此发达,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究其原因,处于河北省中部作为当年北宋边境的一部分,不得不想方设法修建屯田防线,其中就包括挖掘运粮河,既能起到构建军事防线之能,又可以开辟水上航线运送军饷粮草,可谓一举两得。因此,宋朝针对地上河流纵横,陆路交通不便,大兴水路运输,随形就势开挖多条运粮河,将相近河流挖通,成为四通八达的运粮河----调运军粮的水上通道,老百姓俗称赵家河,盖取宋朝乃赵家王朝之意。民间传说,宋朝潘杨两家不和,皇上派杨家押运粮草,派潘家监工挖河,潘家为谋害杨家故意将河挖成“九绕十八弯,弯弯对头”的形状,欲使杨家无法按时完成运粮任务。因战事不断,屯兵宿营之地成为村名,也因河流派生地名较多,诸如堤头村、夹河村、芦村、地圈、淤堤、小店、庄火头,西杜村、大、小北河、淮南、窝头、淤堤、南、北白沙等河流岸边之地成为村名,因此,它们不仅是古河流认知标签和历史的见证,镌刻在地图和路标上,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文脉与图腾,更蕴藏着深厚的寓意,延续着历史文化的秘密,承载着一代代人的乡愁,折射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不可复制、不可再生。
据长辈们传说最繁华的是赵家河和潴龙河两大水系,博野小店村名(建于北宋年间,据传系由本县芦村一户在运粮河边开小店发展成村而得名)西杜村(始建于北宋,因处于运粮河三个渡口附近而得名)}往南流至庄窝头,一南一北数十公里,都是赵家运粮河,因靠近赵家河水路码头,货物吞吐量大而称庄窝头(装货头)命名,听故事的人喜欢问“后来呢?”建于唐朝的夹河村,到了宋朝由于河道变更,被潴龙河和赵家河两河钳夹,曾有“夹河”之称,改为夹河村,再后来,赵家河随之消失,终于沉寂下去,被历史封存,绚烂后成为一个永久地历史符号,而奔流了上千年的历史的潴龙河,更是独领更骚,英姿勃发,历史就是这么巧合,潴龙河好像与宋王朝有某些关联,也许是两条大河东西遥首相望的缘故,人们给潴龙河的传说披上一层面纱,增添了几分神秘。
古老的传说,使潴龙河变得扑朔迷离,神秘而美丽,潴龙河古时候确实是水光波影,野渡横舟,沙鸥翔集,因宋村地处南北驿路通衢的重要位置,官方设置了宋村渡口,呼渡之声惊闻数里,货船往来亦称胜慨。当年村口曾有座东岳庙,“三月二十八日乡民焚香,货物毕集”宋村往西行四十里水陆就是安国市闻名遐迩的祁州药王庙,当时有一种“天下中药不到祁州无药效”的说法,所以,全国各地的药材海运到沧州、天津之后,再用大船运往宋村渡口加工后又返回去……。
后来,由于气候以及上游兴修水库等原因,潴龙河逐渐断流、干枯,记得上小学时候河水在大河床行走,后来上中学、高中时河水很规矩地在小河床游荡,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像地漏一般河里的水越来越少,恰似踩着乡亲们的心尖上流淌,有时雨季河流又复活了,像梦一般,一眨眼,雨季结束,就变成了一条水渠,河流几乎断流,变成一条可怜的小溪。可它毕竟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欢乐与幸福。记得那时,我把手放到河水里,就有鱼碰手指,就用手指夹了,逮住,放到岸边的盆里,然后下河再逮。乐在其中,不知天色将晚。当然,小孩子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有河堤。那时,潴龙河河两岸还有长长的千里河堤,保护着两岸的村庄水大时不被淹没。我的记忆中还没有发大水这样的灾祸,但这却深深地印在了父辈们的记忆当中。1963年,这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常常从父辈们的嘴中讲出来,讲到那时的大水,讲到那时因水而带来的灾荒。从讲述中,我能感受到当时父辈们所承受的那种灾难和刻入肌肤的痛。
1978年是个特别的年份,“一桥飞架东西,天堑变通途,”随着“潴龙河漫水桥”的竣工交付使用,古老的千年古渡口寿终正寝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一些船只浅搁在沙滩上,只有那些散落在沙滩上的贝壳,忠实地展示着当年的王者气派。
如果白洋淀是华北平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那么,潴龙河就是系在明珠上的一条晶莹的彩带。随着雄安新区的崛起,这条注入白洋淀的古老潴龙河定焕发勃勃生机,两岸绿色飘带也定会镶嵌在千里河堤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