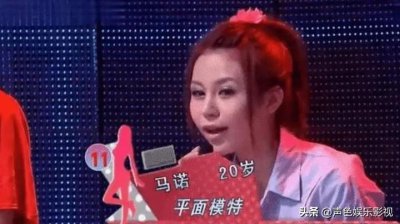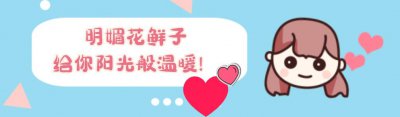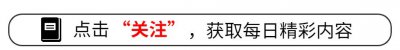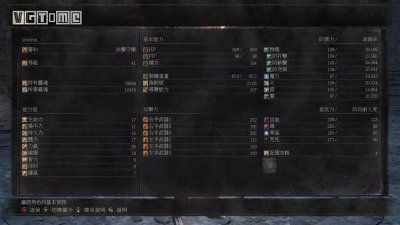《封神演义》中的闻仲形象

《封神演义》立足于“似志在于演史,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1]的创作立足点,塑造了大量的神话形象。《封神》中的闻仲,是刻画得比较丰满的人物形象之一。对于闻仲这一人物形象,学者多以愚忠评价之,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提到“闻太师一味愚忠,而又有一股正直之气”,[2]李建武先生也曾就黄飞虎的革命与闻仲的愚忠作了对比。[3]笔者认为作者如此塑造闻仲,还有内在的历史文化意义和价值。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闻仲的人物形象来着重介绍其内在的历史文化意义及成因。
闻仲在历史上是名不见经传的,他是《封神》中塑造的极具悲剧性的人物形象。从政治地位上来讲,闻仲是帝乙驾崩时的托孤大臣;从师承关系上来说,他是“碧游宫金灵圣母门下,五行大道,倒海移山,闻风知胜败,嗅土定军情”,(第35回)更兼坐骑墨麒麟须臾可至千里之外;从人物性格上来说,闻仲作为殷商重臣,刚正不阿,忠心辅佐纣王统治的江山社稷。可见闻仲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拥有高超的法力和对殷商政权的拳拳忠心。
一、臣之丹心,忧国忧民
起初殷商江山在闻仲等满朝贤士猛将的同心协力的辅佐下,“纣王坐享太平,万民乐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夷拱手,八方宾服,八百镇诸侯尽朝于商”。(第1回)然而在小说开头的古风中 “紊乱朝纲绝伦纪,杀妻诛子信谗言。秽污宫闹宠姐己,蚕盆炮烙忠贞冤。鹿台聚敛万姓苦,愁声怨气应障天。直谏剖心尽焚炙,孕妇剖剔朝涉歼。崇信奸回弃朝政,屏逐师保性何偏。郊社不修宗庙废,奇技淫巧尽心研。昵比罪人乃周畏,沉酗肆虐如鹤莺”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纣王和他的江山早已注定要灭亡的命运,同样,作为忠贞不贰的闻太师,也必然要为君主的社稷献身。
纣王在女娲宫进香祈福时亵渎女娲这位“上古之正神,朝歌之福主”成为了他走向灭亡的导火索。女娲为了惩罚纣王的亵渎神明之举,派了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和玉石琵琶精“隐其妖形,托身宫院,惑乱君心”。(第1回)此后的纣王宠爱由妖精变化的美女,亲信费仲、尤浑这些奸佞小人的行为加速了自己的灭亡之旅。与此同时,纣王诛戮和逼死对自己忠言相谏的杜元铣、梅伯、商容、胶鬲、比干等贤能正直的大臣,建造鹿台,设计酷刑,兴建酒池肉林,甚至为了妲己为首的女妖,戕害姜皇后等。这些罪行与司马迁《史记·殷纪》中所记载的纣王“好酒淫乐,娶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相比,其残暴与荒淫有过之而无不及。
即便如此,纣王对闻仲却是十分敬畏。当闻仲从平定叛乱的战场凯旋的时候,得知纣王的堕落和无道而义愤填膺,上书十策以陈情劝谏,渴望纣王能够迷途知返,拆鹿台,废酷刑,亲君子而远小人。可惜的是,此时的纣王早已在骄奢淫逸中迷失了自我,闻仲虽说凭借自己的威望,可以让纣王“没奈何”,准七件所奏章程,但是当时的殷商政权已成为各方诸侯觊觎的对象,闻仲不得不去平定东海平灵王的反叛。对于闻仲出征,“纣王闻奏大悦,巴不得闻太师去了,不在面前搅扰,心中甚是清净”。(第27回)
当时的殷商的大军中,除了闻仲之外,殷商的可用之才比比皆是。无论是武成王黄飞虎、三山关总兵邓九公还是青龙关总兵张桂芳等人都可以临阵杀敌,保家卫国。但是,黄飞虎、邓九公和张桂芳与闻仲相较,地位、声望和本领远远不及,所以,只有令纣王闻而生畏的闻仲离开朝歌,纣王的残暴与荒淫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闻仲的悲剧命运才能得以继续。
二、命丧绝龙,悲剧形成
闻太师为殷商的江山立下了显赫的功绩。他的本领高强以及他和截教的师承关系却是在与西岐的对抗中显现的。鲁迅先生指出“助周者为阐教即道释,助殷者为截教”,[1]阐教门人(除申公豹等寥寥数人外)均为正直之士;“截教门中一意滥传,遍及匪类”,(第82回)门人亦“不择是何根行,一意收留”。(第77回)作者视阐教为“阐道法,扬太上之正教”,(第5回)而视截教为“左道旁门”。(第37回)小说中的阐教门人与截教门人的斗法占据了周商大军对抗的大半部分场景。阐教门人从数量上来说,比不上羽毛禽兽之辈相杂的截教门人,但是,阐教是作者大力宣扬的名门正教,无论闻仲请来的九龙岛四圣、金鳌岛十天君、赵公明,还是申公豹请来帮闻太师作战的云霄、琼霄、碧霄姐妹,尽管可以在斗阵斗法中占得一时上风,可以凭借自己特定的法术使姜子牙等人差一点死于非命,可最终依旧难逃气绝身亡的命运。这种情形不仅出现在闻仲率领大军讨伐西歧,直到后来,截教通天教主亲自率领弟子与辅佐武王的各教教主展开搏杀,其结果仍旧是仙阵被一一化解,门徒死伤及被俘无数。所以在争斗过程中,闻仲作为截教门下弟子,屡遭败绩就不可避免。对于有着截教弟子与殷商重臣双重身份的闻仲,使代表着与之分庭抗礼的新兴力量的周武王及其支持者必欲除之而后快。姜子牙与武王统领的正义之师步步紧逼,最终闻太师在绝龙岭毙命于云中子之手。
闻仲即使归天,仍然念念不忘殷商社稷。他的魂魄仍旧劝谏纣王“勤修仁政,求贤辅国”。(第52回)后来,他封神台受封雷部正神时,作为助周一方的最高神灵太上元始也评述闻仲:“曾入名山,证修大道,虽闻朝元之果,未真至一之谛,登大罗而无缘,位人臣之极品,辅相两朝,竭忠补衮,虽劫运之使然,其贞烈之可悯。”(第99回)由此可见,作者意在塑造闻仲作为一个注定被天命击败的忠直的英雄人物呈现在读者面前。
三、闻仲愚忠之外的历史文化内蕴
闻仲是一个悲剧化的人物,造成这种悲剧的主要原因正如同李建武先生等人所述的那样,固然是因为他的愚忠思想,但是,笔者发现这其中另有一些历史文化内蕴可堪挖掘。
首先,闻仲的愚忠思想根深蒂固,然而整本小说中无论是为殷商殉国的张桂芳、鲁雄等人,“入首阳山,耻食周粟,采薇作歌,终至守节饿死”的伯夷、叔齐,还是迷途知返的黄飞虎等人,他们的身上都有较强愚忠的思想存在,只是周边特定的环境改变了其中一些人的固有思想。以黄飞虎为例,他的夫人贾氏和他的妹妹、贵妃黄娘娘先后被纣王害死,黄飞虎先是“听得此信,无语沉吟”,(第30回)却又想着“难道为一妇人,竟负国恩之理?将此反声扬出,难洗清白”,(第30回)若非周纪的激将法,黄飞虎恐怕还会继续他愚忠的思想道路,而不会真正明白“君不正,则臣投外国”(第20回)的意义;而黄飞虎的父亲黄滚起初也是满怀愚忠之念,执迷不悟的人。黄飞虎等欲投西岐,行至界牌关,黄滚却要解子回京,黄明、周纪、龙环、吴谦等家将共同努力,烧了黄滚粮草,逼黄滚弃暗投明,才使得黄氏一门能够效力西岐成为现实。尽管如此,黄滚也是叫苦不迭“我中了这伙强盗的计了”,(第33回)全然不认为自己的愚忠思想是错误的。作者虽然总体上肯定归周义士的弃暗投明的做法,但是也表现和流露出与之自相矛盾的内容和态度。当黄飞虎投奔西岐以后,周武王在设宴款待时,也说“君虽不正,臣礼宜恭,各尽其道而已”、(第34回)可见愚忠的观念不仅是闻仲独有,它存在于作品中大多数人的思想里。作者对于被纣王戕害的忠臣贤士,也是持赞扬的态度,这些可以从“生平正直无偏党,死后英魂亦壮哉”、(第6回)“忠臣直谏岂沽名,只欲君明国政清”、(第9回)“忠心自合留千古,赤胆应知重万钧”(第27回)等诗句中看出;在历史上,对于“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篇第十八》)对于伯夷、叔齐,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舆!”(《论语·微子篇第十八》)。可见,作者的这些赞美完全承袭了历史上儒家思想的大圣先师孔子殷商时期的诸位忠臣贤士所给予的高度评价。如上所述,虽然“《封神》直接引用了孟子的‘暴君放伐论’,多次提及‘残贼’、‘独夫’,这是它突破《三国》局限的地方,这说明作者更善于为应该‘革命’的鼓动找理论支撑”,[3]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愚忠观念,以及当中一些弃暗投明的人物形象先前所有愚忠的观念的表现与塑造,皆表现了作者受宋明理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和制约和这一时代环境的影响和限制。闻仲亦是如此,他的愚忠观念从根本上讲与其他殷商的忠臣贤士的观念完全一致,都是被儒家思想所歌颂的,被封建统治者所喜闻乐见的观念。对于成书于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程度的明代时期的《封神演义》来说,愚忠的观念是必定存在于当中人物思想观念之中的。
其次,闻仲归天的地方是绝龙岭,归天之后,他被封为雷部正神。笔者认为,作者对闻仲身份上的认同,无论是绝龙岭还是雷部正神都与“龙”有着密切的关系,即闻仲是“龙”的化身。这是由中国古时候对龙的一种定位引起的,由于古人的生产力不够发达,对自然现象的解读有着较强的局限性。以雷雨这一自然现象与龙的关系为例,“闪电细长勾折的形状,雷击树木时的伟力都会引起古人的惊怖与联想,于是就产生了雨时雷电为龙升天的说法”;[5]无独有偶,汉代著名思想家王充在《论衡·龙虚篇》也说:“见雷电发时,龙随而起;当雷电击树木之时,龙适与雷电俱在树木之侧,雷电去,龙随而上,故谓从树木之中升天也。”“龙”除了兴风雨、触雷电之外,还是吉祥的化身。王充在《论衡·奇怪篇》中提到:“野出感龙,及蛟龙居上,或尧,高祖受富贵之命,龙为吉物,遭加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征也。”而在小说成书的明代来说,“龙”是皇家的绝对象征,“官吏衣服、帐幔,不许用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凤文,违者罪及染造之人”,[7]与此同时,明代颁赐了绣有蟒纹的蟒衣,“所谓‘蟒纹’指的是少一爪的龙纹,而实际上有些蟒纹几乎与龙纹无异”,[6]明代早期,“贵而用事者,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5]其后明代中期,“内阁赐蟒衣,自弘治中刘健、李东阳始”,[5]后来的明世宗、明神宗先后以公开合法的方式赐徐阶、张居正这样的重臣以蟒衣,可见这种近似龙袍的服饰在明代极其尊贵。笔者认为,由于明代“龙”的地位显赫而权威,而本书作者将闻太师的阵亡与封神都巧妙地和“龙”联系在一起,说明在作者笔下,闻仲不仅是殷商的股肱之臣,而且是殷商江山的吉瑞之物和精神所在。闻太师在世时,他的努力可以使纣王的荒淫残暴有所收敛,适可而止;而闻仲丧命之后,不仅纣王的恶行没有了控制,而且殷商江山也在昏君的不可救药以及武王大军的节节取胜中一步步走向了灭亡。
笔者立足于学界前人的成果,结合自己的一些阅读,发现了闻仲身上这种愚忠观念的一些文化内蕴,即闻仲的愚忠与正直不仅是封建社会的忠君思想中必定存在的,而且,他的特殊身份与忠直精神本身就是作者心中的闻仲这一形象所固有的精神定位。